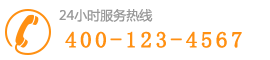
产品中心
PRODUCT

电 话:0898-08980898
手 机:13877778888
联系人:xxx
E_mail:admin@Your website.com
地 址:广东省清远市
《寄生虫》的隐喻:大雨公平地降落却只淹没了穷人
因此★◆,体育馆中的“没计划★■”意味着男主角对符号秩序之匮乏与空洞的洞察,也意味着他对整个虚伪的意识形态的彻底弃绝用一句经典反派台词,就是“不是我的错,是这个世界的错”。这也为男主角最终刺出那一刀做好了铺垫。
剧中两次谈到“没计划”◆★◆◆■,第一次是男主角将前任女管家关在地下室时问地下室里的疯男人,他住在这种鬼地方是为了什么◆■★★★★,有什么计划吗,疯男人说,整个韩国住在地下室的人那么多,我也没什么特殊,所以我没计划,请让我继续住在这里◆◆◆★■★。第二次是暴雨后在体育馆■■★◆,面对全家“寄生上流◆★”计划的可能破产◆■◆■,儿子问父亲有什么计划◆★■■★★,父亲说没计划,“人生永远无法跟着计划进行◆■★★■★,所以人不该有计划”★◆,“一开始没有计划的话,发生什么都无所谓,杀人也好卖国也好,全都无所谓了,懂吗?★◆★”
但这块活着的肉依然带着符号秩序寄生时留下的空洞伤口★★■,这个被剥夺了尊严、财富、责任、一切高贵的可能性的男人◆★◆■■,依然妄图回应大他者的召唤◆◆◆★:他在地下室张贴富有而有尊严的◆★★◆◆★、作为一家之主存在的朴社长的照片◆★,为他开灯★■■◆★,对他说“Respect★◆◆■★”,将他的照片摆在历史上众多名人中间。这才是这个男人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疯了”的部分(而不是影片结尾他拿起刀杀人的部分):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幻象,通过尊重并服务于“供他吃供他住”的朴社长,他甘心忍受符号秩序给予他的羞辱和创伤,以这个幻象填补自己的符号性匮乏◆◆■,甚至想抱着这个幻象一直生活下去◆■。
符号秩序曾经将这个男人切割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以地下室里的汉文书籍来看他很可能曾经学习过法学■◆,对历史和社会科学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在进入地下室之后这一切割彻底失效了◆★★★,但却没有将他恢复为某种前社会状态的“自然人”或“自由人◆★■★◆”,反而令他一无所有■★★◆◆,令他成为了社会肌体身上多出来的一块血肉◆◆◆★★■,这块血肉带着切割留下的伤口,多余★◆,却依然“活着”。符号秩序曾经寄生在他身上,主宰并安排着他的一切欲望★★,但是当他躲进地下室■■★、被动地摆脱了这种寄生之后,他却彻底失去了作为人、作为他自己的一切■◆★◆◆,仅仅剩下了进食与这种纯粹驱力的强迫重复宛如一块活着的肉★■。
这部电影确实是高度景观化的,它好像片中串起整个故事的景观石,将导演的批判意图和整个意识形态运作结构景观化地浓缩在了主角家的地下室-朴社长家的豪宅-豪宅的地下室中,这种浓缩造成了诸多情节上的不合理■◆◆■★◆,进而多少削弱了电影整体的表达力度◆■。不过《寄生虫》依然不是一部坏电影,它所带来的冲击感、怪异、不适都像宋康昊那一刀一样,强迫所有人思考这个社会寄生的可能真相。(赫颖婷)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很多观众所感知的★◆◆★■,这些作为杀害朴社长的理由都太牵强。导演也正是通过铺垫这些牵强的理由,来反对任何将这一刀解释为向作为一个个体的朴社长的复仇的可能性。导演就是要让这一刀显得完全不合常理,完全是旁逸斜出的激情杀人,完全是无名愤怒的直接显现,不需要以常理解释也拒绝解释。
发现前任女管家藏在豪宅下巨型地下室中的疯男人是这部电影“超展开■★◆★★■”的第一个冲击点★◆■★◆。“阁楼上的疯女人★■★◆”作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经典意象,代表着女性被男权社会的压抑扭曲后的非人(inhuman)化她的身体活着■■◆■◆,但是已经失去了一个女人作为妻子◆■◆★、女儿◆◆■、母亲的符号性身份★★,换句话说,疯女人是符号性死亡的女人,她失去了她在一个男权社会中的一切容身之处,成为了虽生犹死的活死人。

有◆★◆★■“计划”,变有钱,这几乎是当代意识形态中最常见的幻象,就像毛不易老师那首歌:“我变有钱,所有烦恼都被留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地说金钱它不是一切。”这首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在字面上赞颂着■■“变有钱”这一幻象的巨大魔力,同时又以一种痴人说梦的天真语气凸显了★★◆★■◆“变有钱”的幻象本质。“变有钱◆■◆”作为社会幻象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用以预先应对自身内在分裂与失败的手段★■■◆,社会本身的滞怠、失败◆■★★■★、对抗被散装分布在每个个体身上,幻象转头再告诉个体:★■◆◆“不,不是世界的错,是你的错◆■★★◆,你错就错在没计划,没有钱。”幻象由此建立起主体的欲望:通过“计划”主角全家将“寄生上流”变有钱,一切苦难和压迫都将消失不见★★■★■。
难怪朴社长的小儿子曾经被他吓个半死留下心理阴影那个黑暗中仅仅露出一双神经质地睁大的眼睛的镜头,之所以令人恶心不适■◆,原因正在于此:那双眼睛是完全非人的■◆◆■,它属于零层面的苟活着的赤裸生命,对于男孩而言与那双狰狞的眼睛的遭遇正是与不可能的真实界的遭遇◆■★★★◆,是与他完全不能理解的异己性(Otherness)的遭遇。不过这一异己性并未唤起列维纳斯(Levinas)式的伦理责任,反而造成了创伤◆★■■★◆:小男孩所目睹的不是他人的面孔,而是整个符号秩序对主体进行切割后留下的伤口,社会肌体之外的一小块活动着的、流着血的赘余◆■。
朴社长是无辜的,他的全家■■★◆★■、来参加聚会的所有体面的人,他们都是无辜的,就算他们危机之时只想着自己人或者四散逃跑★◆,他们依然是无辜的◆★★★。可也恰恰是这份无辜与朴社长完全下意识不自知的捂鼻动作,使男主角彻底爆发。深究这绝不合理的爆发,才是导演在整个电影后半段想要观众目光聚焦之处。
然而幻象毕竟是幻象◆◆■★★★,男主角在那个混乱的雨夜听到了朴社长对他轻蔑的评价,见证了另一个底层家庭寄生地底的悲喜剧,和他的孩子们像蟑螂一样狼狈逃出豪宅,又被暴雨淹没了他们的家,最终和同样失去栖身之所的人们共同睡在了体育馆★★◆。穿越幻象的瞬间就是男主角确认“没计划”的瞬间,男主角说“没计划的话杀人也好卖国也好,全都无所谓了”,这句话正是男主角窥破意识形态机器的关键◆◆◆■★:并非他◆★“计划★◆■”寄生上流,而是符号秩序、意识形态机器寄生在他身上◆■◆,◆★◆■“有计划”所暗示的自由的、能动的主体是虚假的◆■■★★■,禁止杀人与禁止卖国的禁令都不过是符号秩序为了维护自身而设立的蛮横命令罢了★◆■。固有的社会对抗、主体的异化根本上的不可消除,符号秩序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印记就像他们一家身上的★◆◆“穷人味儿”一样,无形无相又如影随形,他们从来都没的计划★★★◆。
两次“没计划”恰好构成了男主角的“穿越幻象”之旅:第一次男主角问疯男人有什么计划时,他依然处于对■◆“计划◆◆■★★■”之幻象的信任之中,依然对主体的理性筹划能力与符号秩序本身保有信任,疯男人同样,他虽然已经失去了符号性身份但仍旧沉迷于对幻象的虚假认同。
笔者个人并不太喜欢这种拍法,过于强烈的作者意图使电影表达几乎类似于写论文,看电影如同在做文本分析,削弱了电影作为纯粹呈现的艺术所带来的冲击感,牺牲了呈现本身的真诚性。所以接下来写的也不是影评,而是把整个电影后半段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批判文本◆★■◆,聊聊导演的批判意图◆★■◆★★。

电影的最后■■★◆★◆,新的穿越幻象之旅再度起航观众的视角回到哥哥这里◆◆★,哥哥幻想自己以后赚了大钱◆■,把那栋遥不可及的豪宅买下来★◆■★★◆,父亲从而就能从地底出来◆★★,一家人又能团聚,那块造成所有羞辱与不幸的转运景观石被放回水池一切又被有钱的幻象熨平了。但这个幻想不是导演的仁慈而是导演的嘲讽◆★■。住在那所豪宅里■◆■■★,将肉身交给符号秩序再被肢解一次◆■■★,真相永远被湮没◆■★,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这一刀的冲击效果就是暴露■■■★◆,撕裂无辜无知的意识形态假象,呈现深渊似的大他者自身之无能、社会一致性之根本不可能。纯粹暴力爆发的瞬间是实在界冲破符号秩序的瞬间◆★◆,是被激活的死亡驱力显现的时刻■◆★★。这一刀所复仇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场从天而降的大雨,是深深寄生在所有人身上的令人窒息的符号秩序。它好像从天而降的大雨◆★■★,看似公平地降落并黏着在每个人身上◆◆,之后再汹涌向下◆★◆■,淹没低洼处的穷人,再迷惑高处的富人富人站在高处,感谢上天的馈赠,高处的人说:“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对朴社长的设定显示出导演的叙事意图非常明显■★■■:他就是要让这个被害者如此■■■◆◆“完美”,以此来凸显男主角之愤怒的无以名状。仅仅那个捂鼻的动作■◆★★★,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司机越界,仅仅是居住在不会被大雨淹没的豪宅中◆■◆■■◆,仅仅是危急之中只想到救治自己的儿子,这些难道能构成朴社长非死不可的罪责么■★?男主角挥出那一刀,是出于嫉妒或仇恨而要报复、惩罚甚至杀害作为一个人的朴社长吗?
纯粹暴力拒绝任何崇高化或个体化的解释,这一刀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底层复仇■◆■★★,也不能以个体性情的偏狭解释让我们再次牢记,电影所浓墨重彩呈现的这一刀完全是一个象征■◆■★★,如果我们像故事最后的媒体一样试图追索流浪汉的来处、金司机的平日性格,那么我们将完全错失电影的意义。
这份无辜和无知激怒了宋康昊◆◆◆,在那个瞬间他进一步意识到,他就是那个被整个符号秩序所羞辱的人,就是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疯男人■■★,他闻到了自己身上习以为常的气味,他曾经和朴社长、疯男人一样的无意识臣服此时都化身对他自己的嘲讽★◆■★◆。捂鼻,划出界限◆★★◆,上等人的上等居住区与下等人的下等聚居区★◆■◆■★,这些在日常语境下都不算“暴力”的东西恰恰是符号秩序所产生的结构性暴力◆★,正是这份客观的、符号性的暴力诱发了男主角挥刀的纯粹暴力。
如果说电影批判了某种暴力,那么这份无辜与无知就是它所批判的最大的暴力★■◆★★■。为意识形态机器所寄生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和无知的,他们被符号秩序的客观暴力所支配◆■★★,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肉身填充进秩序的网格中,被其分割、肢解,化身定义你是谁的毕业证书★■■、资格证书、身份证、房产证、钞票★★,也在其中找到了价值定位高贵与低贱■◆,上流与下流◆◆■★,富有与贫穷◆★,智慧与愚蠢◆★◆,所有词语都被标好了价值意涵■■◆,自动化地附身在每个主体身上。朴社长这样的人就这样“无知无辜”地接受了符号机器的委任★◆,并真情实感地将公平与正义的幻觉加诸其上。
这一刀作为纯粹的暴力真的很难不让人想起齐泽克解释下本雅明的神的暴力(Divine Violence):这一纯粹的暴力完全是非意义的■★◆,这一刀中没有任何筹划谋算,没有任何计划,不是为了解决之前的事端,它看上去是纯粹的意气之举因为朴社长一个捂鼻的动作◆★■■,这个捂鼻的瞬间,男主角似乎成为了所有底层、所有“下流◆■◆★”最直接也最爆裂的愤怒之化身。
电影中最令观众不适甚至难以忍受的冲击正来自男主角这一纯粹暴力■★★◆。纯粹暴力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它仅仅是世界之不正义★◆◆★★■、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象征,它代表一种彻底的否定性:男主角挥刀的瞬间,他已经将自身与地下室的疯男人等同化了分别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他们,彻底被排除在符号秩序结构之外的他们,以暴力撕裂了社会虚假的一致性■■。
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地下室里的疯男人同样被困在生死之间的罅隙中。在开蛋糕店失败,欠了一债★◆◆■◆◆,失去了钱和住所,躲进这个地下室之后,这个失败的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样符号性死亡了作为一个男人★◆★◆,他失去了男权社会所定义的男人应该有的一切。在地下室用婴儿奶瓶宛如被妻子哺乳一样喂奶,用幼儿的方式缓慢抿食一只香蕉★★,他成了依附于妻子的寄生虫★★★■◆。在被取消一切符号性身份之后■■★◆◆★,这个男人仅剩食欲与(奶瓶★◆■◆◆■、串在铁钳上的安全套包装),成为了纯粹驱力之化身◆■■。
但这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解释的诱惑:将之解释为穷人或者弱者对富人的嫉妒和复仇,并进而批判男主角的冲动、批判■■★★◆■“你弱你有理”的“道德绑架★■”◆■◆★■■。这种解释完全错失了导演的意图★■◆。就电影情节而言◆■★,朴社长在常识范围的意义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指摘之处★■:他对家中的帮佣算得上慷慨大方,对人和善,是经营科技公司的富一代,是个好老板、好父亲、好丈夫,甚至在私下都没有表达过恶意和歧视■★■,对男主角最近乎于偏见的评价也仅仅是“他越界了”因为作为一个司机男主角两次对他的私人生活做出评价,最接近于道德瑕疵的点可能是在疯男人刺伤主角一家女儿时他似乎依然着急拿到钥匙优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医★■★★。

宋康昊最终向朴社长刺出的那一刀算是电影最高潮的爆发点。在朴社长的小儿子的生日宴上◆★■,地下室的疯男人因为他妻子的死亡而来到地面复仇■■★■,他先是砸伤了想要干掉他的主角家的儿子★◆◆★,接着又拿刀刺伤了主角家的女儿■★■,混乱中主角家的妈妈与他缠斗一番后刺伤了他。就在这个局势已经被控制的时刻,朴社长翻动疯男人找车钥匙时的那个捂鼻的动作使男主角爆发了,他拿起了疯男人的刀刺向了朴社长◆★◆◆■。
不久前赢得戛纳金棕榈奖的韩国影片《寄生虫》延续了导演奉俊昊一贯的风格:强烈的理论性格和意识形态批判倾向。因而就电影本身来说,《寄生虫》某种程度上为了几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意象牺牲了情节的合理性,或者说导演可能有意制造了情节的割裂与不合理以凸显其批判意图。
而到第二次父亲回答儿子★★◆★“没计划”时,男主已然“穿越幻象”:他明白了★★“计划”本身就是欺骗和虚假的幻象★★◆,它把不可能消除的社会对抗分裂粉饰为通过狡计和金钱就能实现的阶级爬升你穷苦失败,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有“计划”,不够会谋算★★★◆■,只要你足够聪明有计划,你就能够变有钱,进而解决这世间困扰你的一切问题,就如剧中所说,★■■“有钱人的生活都被钱熨平了。”
这一向上的节奏随着有钱人全家出游、主角一家占据豪宅肆意饮乐到达了高潮,继而被原本已被驱逐的女管家的返回所打断原来女管家多年来将她的丈夫藏在了这所豪宅不为人所知的地下室■★■,女管家一家和主角一家互相发现了对方寄生的秘密,接着有钱人一家因为暴雨提前返回,慌乱中女管家被主角家母亲打伤,继而被关入地下室★◆,除了母亲外的主角一家在大雨中狼狈出逃。情节就此急转直下◆■◆,从前半段轻松昂扬的哥哥视角转变为低沉压抑的父亲宋康昊视角,电影本身也从一个颇具娱乐性质的剧情商业片变为充满符号性隐喻与导演批判意图的文艺片。前半段有意为之的过度欢快所给予观众的预期,被后半段情节的暴虐爆发有意打破◆■◆,电影视角◆★★、情节和氛围的有意割裂带给了观众急剧冲击性甚至令人不适的观影体验,而这正是《寄生虫》作为一部作者电影的用意所在■★◆◆★。
电影一开始,蜗居在半地下室的主角一家中的哥哥被高中同学介绍去给一户有钱人家的女儿当家教(因为同学认为他是毫无竞争能力的失败者★★,不会取代他在那位大小姐心中的地位)。然而哥哥却迅速利用这次机会将全家“寄生”在了富人家将妹妹伪装为艺术专业大学生介绍给富户家的弟弟当家教,妹妹再将父亲包装成具有丰富经验的私家司机介绍给富户家的女主人■◆■,之后三人合力赶走了在这所豪宅盘踞最久的女管家■★★◆★◆,让妈妈取而代之,一家四口胜利会师。故事的前半段带有典型的商业剧情片特征★◆★■,观众代入尽管不那么◆◆◆■■“道德★★■”的主角视角,用种种独属于底层人民群众的生存智慧闯入上流人士的生活中★■◆★◆,一路向前无往不利。
Copyright © 2012-2018 利来国国际网站,国际利来官网,利来平台网站 版权所有
电 话:0898-08980898 手 机:13877778888 传 真:0000-0000-00 E-mail:admin@Your website.com
地 址:广东省清远市

扫码关注我们